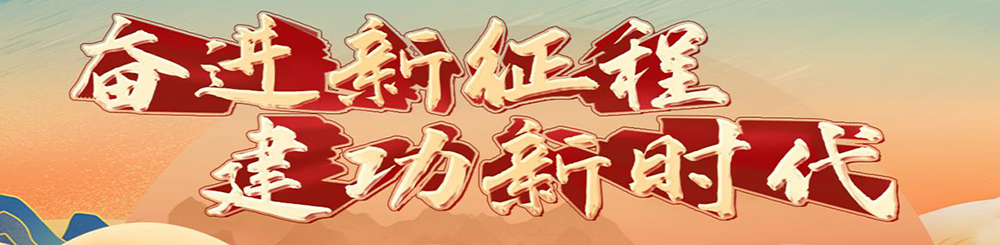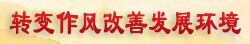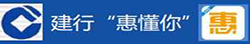清代絲路紀(jì)行詩(shī)的主旋律
編輯:魏少梧 信息來(lái)源: 西e網(wǎng)-光明網(wǎng)發(fā)布時(shí)間:2019-1-22
清代絲路紀(jì)行詩(shī)人的構(gòu)成復(fù)雜,包括軍旅詩(shī)人、戍邊官員、游幕投邊文人以及清廷流人,而以流人群體中詩(shī)人的規(guī)模最為龐大,詩(shī)作水平也較高。在這些絲路詩(shī)人中,最為人所熟知的就是乾隆年間紀(jì)昀創(chuàng)作的《烏魯木齊雜詩(shī)》160首。此外還有洪亮吉《伊犁紀(jì)事詩(shī)》42首,祁韻士《西陲竹枝詞》100首,福慶《異域竹枝詞》100首,林則徐《回疆竹枝詞》24首,葉禮《甘肅竹枝詞》100首,王曾翼《回疆雜詠》30首,左肇奎《伊犁紀(jì)事》20首,蕭雄《西疆雜述詩(shī)》150首等。
清代絲路紀(jì)行詩(shī)題材大為拓寬,內(nèi)容豐富多彩,凡山川之走向、關(guān)塞之險(xiǎn)要、物產(chǎn)之分布、民族宗教之關(guān)系、風(fēng)俗習(xí)慣之異同、政略軍略之得失皆囊括其中。由于遠(yuǎn)離中原,而且地域非常遼闊,旅途漫長(zhǎng)而艱辛,行旅絲路的文人只得以詩(shī)自?shī)?,正如祁韻士所言?ldquo;長(zhǎng)途萬(wàn)里,一車(chē)轆轆,無(wú)可與話,乃不得不以詩(shī)自遣。”(《蒙池行稿》自序)再加上路上絲綢之路在漫長(zhǎng)的歷史時(shí)期內(nèi),曾是中原溝通外國(guó)、對(duì)外開(kāi)放的唯一通道,有著豐富的歷史遺存和文化遺產(chǎn),詩(shī)人所到之處,山川、風(fēng)物、土俗、民情、古跡等無(wú)不激發(fā)著他們的創(chuàng)作熱情。而絲綢之路自漢唐以來(lái),就是多種文化匯聚、碰撞、融合的關(guān)鍵地帶,至清代已經(jīng)形成了與中原迥異的多元文化品格,所以清代絲路紀(jì)行詩(shī)作當(dāng)中,詩(shī)人們幾乎將一路上的所見(jiàn)、所聞、所感毫無(wú)遺漏地形諸筆墨,吟成詩(shī)篇。
清人的絲路紀(jì)行詩(shī)作中,清代西北邊疆發(fā)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有所反映,有些詩(shī)作堪稱(chēng)“詩(shī)史”,如左宗棠的幕僚施補(bǔ)華所作的《重定新疆紀(jì)功詩(shī)》,敘述了左宗棠統(tǒng)領(lǐng)西征軍收復(fù)新疆的全過(guò)程,此詩(shī)為四言長(zhǎng)詩(shī),共280句,凡1120字,其認(rèn)識(shí)價(jià)值不可低估。同時(shí),河西走廊、天山南北地理環(huán)境千差萬(wàn)別,戈壁、草原、雪山、沙漠、綠洲等地貌交相呼應(yīng),獨(dú)特的地理風(fēng)光在詩(shī)人筆下形成了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詩(shī)歌風(fēng)貌。而絲綢之路自古又是多民族共生共存、共同發(fā)展的黃金地帶,多民族聚居的民俗事項(xiàng)也成就了清代絲路詩(shī)歌創(chuàng)作的一大特點(diǎn),民族習(xí)俗、宗教信仰等皆成為清代詩(shī)人吟詠的對(duì)象,甚至很多詩(shī)人直接用少數(shù)民族語(yǔ)言和方言入詩(shī),凡此種種皆造就了清代絲路紀(jì)行詩(shī)歌獨(dú)特的風(fēng)格。
就詩(shī)人自身創(chuàng)作風(fēng)格而言,絲綢之路上的壯美風(fēng)光、深厚的歷史積淀,又陶鑄了他們的審美趣味,影響詩(shī)人的創(chuàng)作觀念和風(fēng)格,許多詩(shī)人在行旅絲路之后,創(chuàng)作更上層樓,洪亮吉即是一例。論者對(duì)其絲路紀(jì)行詩(shī)評(píng)價(jià)甚高,如“塞外諸詩(shī),奇情異景,窮而益工。”(《國(guó)朝詩(shī)萃二集》),“至萬(wàn)里荷戈,身歷奇險(xiǎn),又復(fù)奇氣噴溢,信乎山川能助人也。”(《聽(tīng)松廬詩(shī)話》)
清王朝是中國(guó)歷史上最后一個(gè)專(zhuān)制王朝,在其近三百年的歷史當(dāng)中,發(fā)生了不計(jì)其數(shù)的重大事件,而再次統(tǒng)一西域、打通絲路,毋庸置疑地成為清王朝最值得肯定的歷史貢獻(xiàn)之一。乾隆二十四年(1759),在經(jīng)歷了天山以北兩討厄魯特蒙古準(zhǔn)噶爾部、天山以南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之后,清代中央政權(quán)終于統(tǒng)一天山南北,將河西走廊所連接的西域廣袤的疆域再度納入中央王朝的版圖。乾隆二十九年(1764),御史曹學(xué)閔建議重修《一統(tǒng)志》,其理由就是要將剛剛重新統(tǒng)一的西域納入到《大清一統(tǒng)志》,“以昭大一統(tǒng)之盛”(《大清一統(tǒng)志序》)。乾隆四十九年完成的續(xù)修本《大清一統(tǒng)志》,專(zhuān)門(mén)以七卷的篇幅設(shè)立了“西域新疆統(tǒng)部”,這次重修“體現(xiàn)了大一統(tǒng)版圖的完整以及西域少數(shù)民族地區(qū)與祖國(guó)不可分割的血肉聯(lián)系,從而貫徹了國(guó)家大一統(tǒng)的纂修宗旨”(星漢《清代西域詩(shī)研究》)。乾隆皇帝還頒旨對(duì)西北進(jìn)行實(shí)測(cè),將西域各地的節(jié)氣時(shí)分補(bǔ)入《時(shí)憲書(shū)》,新疆輿地收入《內(nèi)府輿圖》,這些措施都宣示著疆域統(tǒng)一之后,政治秩序的全面建立和政治地域的認(rèn)同。嘉慶十七年(1812),嘉慶帝命令穆彰阿等再次重修《大清一統(tǒng)志》,將“西域新疆統(tǒng)部”明確為“新疆統(tǒng)部”。清代確定的“新疆”,并沒(méi)有新辟疆土之意,同光年間平定張格爾之亂、抗擊沙俄侵略的陜甘總督左宗棠總結(jié)得好,他稱(chēng)為“故土新歸”確切地反映了中原士人對(duì)待這片區(qū)域的認(rèn)識(shí)和歷史情感。
縱觀絲綢之路的歷史盛衰我們會(huì)發(fā)現(xiàn),國(guó)家的統(tǒng)一安定是絲綢之路暢通、繁榮的根本前提,和平共處、互惠互利、平等交流是絲綢之路上的各國(guó)家、民族在歷史實(shí)踐中達(dá)成的共識(shí)。因此,追求和平與統(tǒng)一、反映交流與認(rèn)同,是整個(gè)清代絲路文學(xué)的主旋律。
首先,清人絲路文學(xué)的主題表現(xiàn)上,除了傳統(tǒng)的風(fēng)光紀(jì)游詩(shī)作以外,大量的作品所反映的是絲綢之路上的各民族共同開(kāi)發(fā)西北邊疆、友好交往,以及在文化、宗教等方面的相互理解和認(rèn)同的社會(huì)生活場(chǎng)景。這些描述不僅是國(guó)家大一統(tǒng)局面下的潤(rùn)色鴻業(yè)、歌功頌德,更深層地反映了諸多中原士人身履目驗(yàn)、實(shí)地體會(huì)之后的真切體會(huì)。他們的創(chuàng)作,無(wú)一例外都在向我們傳遞一個(gè)理念,邊疆的鞏固和繁榮,最根本的前提就是國(guó)家的統(tǒng)一和民族的團(tuán)結(jié),諸如周珠生“且喜皇圖無(wú)內(nèi)外,笑他秦帝筑長(zhǎng)城”(《呼圖壁貽施巡檢》),即暗含此意。
其次,創(chuàng)作視角的轉(zhuǎn)換上,清代絲路文學(xué)的創(chuàng)作者也有了新變。版圖的統(tǒng)一,疆界的明確和國(guó)家意識(shí)的增強(qiáng)都對(duì)清代的絲路詩(shī)人產(chǎn)生了很大影響,這體現(xiàn)在清代詩(shī)人理解和審視乃至記錄、評(píng)價(jià)絲路社會(huì)生活的時(shí)候,其身份和立場(chǎng)的改變。他們的身份從旅行者、外來(lái)客變成了主人翁。有了這樣的認(rèn)識(shí),他們看待邊疆風(fēng)物、少數(shù)民族文化,更多的是本著寬容的善意去觀察,是以“同胞”的立場(chǎng)去理解和認(rèn)同,如施補(bǔ)華《輪臺(tái)歌》有句云:“衣冠大半仍胡俗,郡縣從新隸職方”,即反映了中央政權(quán)雖然設(shè)立郡縣、統(tǒng)一了政治區(qū)劃,但還是尊重少數(shù)民族習(xí)俗,說(shuō)明清代文人已逐漸將以漢民族為主的視角轉(zhuǎn)換為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視角。
再次,意象選擇上,反映出清代詩(shī)人進(jìn)步的民族文化心態(tài)。在傳統(tǒng)的絲路文學(xué)作品中,尤其在邊塞詩(shī)作當(dāng)中,絲路上的陽(yáng)關(guān)、樓蘭、塞外、孤城、陰山、沙場(chǎng)、胡虜?shù)纫庀?,往往傳達(dá)給讀者的是一種荒涼、冷寂的感受,使人感覺(jué)西域是一片不毛之地,陽(yáng)關(guān)之外的少數(shù)民族是未開(kāi)化的蠻族。這是由于絲綢之路上的地理特征與中原差別較大,而中原與西北邊疆的民族交流由于絲綢之路的斷絕又較少的緣故。清代統(tǒng)一西域之后,經(jīng)濟(jì)發(fā)展的同時(shí),中原與絲綢之路上各民族的交流也越來(lái)越頻繁,所以清代文人對(duì)這片廣袤的土地更加熟悉,他們的詩(shī)作有意消除了邊地與中原的隔膜感,通過(guò)對(duì)邊疆風(fēng)物的描述,不再刻意放大文化、地理環(huán)境當(dāng)中的“異質(zhì)”特征,表現(xiàn)出了一種求同存異、民族共融的態(tài)度。在他們的詩(shī)作之中,雖然傳統(tǒng)的邊塞意象仍在使用,但其蘊(yùn)含的文化心態(tài)卻早已改變。“衣冠通日下,風(fēng)景似江南”(畢沅《抵迪化城有作四首》)、“春度玉門(mén)關(guān)外滿,不須聽(tīng)作戰(zhàn)場(chǎng)聲”(和瑛《聞城上海螺》)、“祁連山上春如海,開(kāi)到江南桃李花”(鐵保《次及門(mén)阮中丞寄懷原韻》),這樣的描述拉近了中原與邊地的距離,也還原了一個(gè)較為真實(shí)的絲路面貌,更重要的是體現(xiàn)了清代士人進(jìn)步的民族文化觀,體現(xiàn)了詩(shī)人們對(duì)邊疆文化環(huán)境的認(rèn)同。
作者:侯冬(西北師范大學(xué)文學(xué)院副教授)
《光明日?qǐng)?bào)》(2019年01月21日13版)
原文鏈接:http://news.gmw.cn/2019-01/21/content_32380935.htm
熱門(mén)資訊